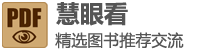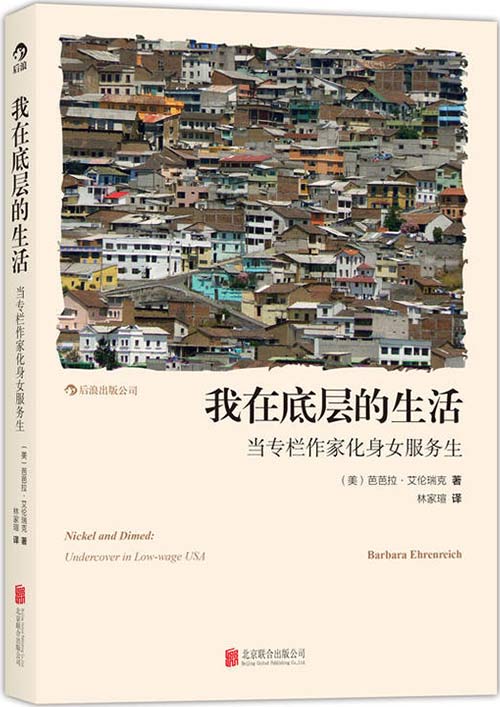
编辑推荐
推荐一:“越贫穷越工作”的口号 VS “越工作越贫穷”的现实
推荐二:努力工作就能改善生活,是否已经沦为一句谎言?
推荐三:这不仅是美国底层民众的故事 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
推荐四:盘踞亚马逊畅销书榜长达12年
全球已有英、法、日等14个语言版本
内容简介
失业必然导致贫穷,努力工作就一定能改善生活吗?在美国,数百万的底层劳工终日工作,却只能赚得每小时6—7美元的时薪,他们要如何生存,又是否能够走向成功?
为了寻找底层贫穷的真相,作者隐藏自己的身份与地位,潜入美国的底层社会,去体验底薪阶层是如何挣扎求生的。她为此制定了严苛的执行标准,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做出相应调整,力求贴近低薪阶层的生存实态。在化身底层劳工的这段期间,作者流转于不同城市、不同行业,先后当过服务员、旅馆服务员、清洁女工、看护之家助手以及沃尔玛的售货员,也遇到了许多拥有不同背景、个性迥异的上司与同事。作者将自己在基本生活线上挣扎的经历描述得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,又出乎意料地幽默,展现了底层劳工在薪资、住房、医疗、雇佣关系等各方面的生存实态。
作者简介
芭芭拉 ·艾伦瑞克(Barbara Ehrenreich),美国畅销书作家。1941年生,洛克菲勒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,女性主义者、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。曾任《时代杂志》专栏作家,作品常出现在《哈泼》《国家》《新共和》等重要刊物中。她出身底层,父亲是矿工,前夫是卡车司机,因此特别关注美国底层社会的生活。至今已出版21本著作,代表作有《纽约时报》畅销榜作品《M型社会白领的新试炼》(Bait and Switch: The [Futile] Pursuit of the American Dream,2005)、《失控的正向思考》(Bright-Sided: How the Relentless Promotion of Positive Thinking Has Undermined America,2008)等。
译者:林家瑄,1973年生于台湾新竹,台湾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硕士,曾任艺术行政、期刊编辑,并从事翻译。译作包括《两位严肃的女人》《少年罗比的秘境之旅》等。
目录
前 言
致 谢
序 章 准备开工
第一章 在佛罗里达州当服务员
第二章 在缅因州擦擦抹抹
第三章 在明尼苏达州卖东西
第四章 成果评估
出版后记
前言
前 言
不同于电视情景喜剧和好莱坞电影中的美国,另一个美国是一个被其自身忽视的隐密大陆。很少见诸报道的关于美国梦的真相就是,这个国家也存在着分布广泛、不断增长和不可避免的贫穷。在这个国家中,那些做着基础工作的人们,只能拿到低于生存标准的薪资。
芭芭拉·艾伦瑞克潜入最低收入人群的生活,那里的人们整日工作,挣扎着想要在社会上获取一个立足之地。她先后当过女侍、旅馆房务员、看护之家助手和沃尔玛的售货员,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任劳任怨、需要付出艰辛劳动、没有晋升阶梯的底层世界。从佛罗里达到缅因,再到明尼苏达,她在贫富领域的发现是十分令人震惊的。对一个健康的单身女性来说,她所得到的报酬并不足以养活她自己。甚至,对于那些住在廉租房、汽车旅馆、房车公园的人来说,他们做着一份累得自己腰酸背痛却只有最低报酬可拿的工作,所赚的钱还不够支付房租、交通费和食物费。低收入者们是如何生存的?答案是他们根本生存不下去。只有那些身体强壮得足以做两份工作,或是能与别人合租房子的人,才能够生活得下去。
艾伦瑞克对那些丑陋可恶的雇主的描述,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她曾在一家名叫“女仆”的清洁公司工作,依照严格的规定清扫工作必须快速完成,而且一整个房间只能使用小半桶脏水,还要背着像机关枪一样重的真空吸尘器,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冲刺。这些房屋清洁公司,雇佣了大量穿着闪亮工作服、领着微薄工资的员工,来为那些因为过于富有和忙碌而没时间自己打扫的人清扫他们的家。这些构成了美国高级住宅的生命维持系统,也严重损害了那些清洁女工的身体健康。
雇主们付给员工的薪资越少,就会越急着去榨干他们的每一滴汗水,每分每秒都以一种侮辱性的方式监管着他们,而这种侮辱性的方式若再进一步,恐怕没有哪一位工人可以忍受。当没有客人时,一个女服务员可以坐下来休息?不可以,想都别想!雇主们总可以找到些事让她保持忙碌的。有一天,艾伦瑞克独自一人被留在看护之家,去应对一大群神志不清的老年人。又有一天,她试图分担一位受伤的(而且是怀孕的)女同事的工作,而这位女同事则担心一旦暴露了自己的体弱,就会丢掉这份工作。艾伦瑞克还有一位同事非常贫穷,以至于每天的午饭都只吃一包“立体脆”。
艾伦瑞克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记者,也能对其所揭露的社会经济的怪异之处做出犀利的评论。她预先假设,若一个富裕地区存在劳力短缺的状况,当地薪资一定会上涨。当然,在单纯的资本主义模式下,一个紧俏的劳动力市场会倾向于开出最低薪资吗?所以,她前往满被招工广告覆盖的明尼苏达州,最后在沃尔玛找到了一份低于生存标准的时薪7美元的工作。她发现,她的一些同事可能正住在慈善收容所中。当劳工在供需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时,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?这是因为穷人并不是理想的市场模型,他们太贫穷了,以至于只能在一份份工作中仔细挑选。这些勉强维持生计的人,不敢冒着失去一周薪资的危险去换工作,担心会被人从租房中赶出去或是挨饿。想要仔细挑选更好的工作机会,就意味着会有冗长的申请、面试、羞辱人的药物测试和等待——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,这些不是他们能负担得起的。雇主们谋算着要降低工资,却不把工资标准张贴出来,这就是使得雇员没办法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可去的——当然也没有工会。在几乎没有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,人们出行依靠自行车或是搭朋友的顺风车。他们不可能对整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冲击,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市场中,劳动力并不会像资本一样随着机会的起伏而发生移动。
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,就近年来生产效率的增长而自我称贺:《纽约时报》报道说,“在全国的工资数据统计中,通货膨胀引起的工资涨幅是不明显的”,并引此作为经济健康的一个信号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有最低工资标准,而90年代的经济繁荣已经受到了最低工资标准实际水平下降的刺激:现在的低收入者所挣的钱实际上只有30年前的91%。在美国福利制度的新规定下,一个人最多只能接受5年的国家供养,大量的家庭将要被驱逐出福利系统名册,艾伦瑞克记录下了在他们身上将会发生些什么。即便他们找到工作,甚至工作一辈子,从来不撤回社会保障金,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有足够的钱买食物。他们没办法勉强过活。
英国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不同呢?如同美国一样,这里的贫富差距也在持续增长。1/3的劳动力所挣的薪资,低于欧盟的“体面”工资指数平均值的60%;而且对于居于社会经济最底层20%的人来说,很少会有晋升或离开的机会。拿着低薪资、做着不稳定工作的人们,会在绝对的贫穷线上下挣扎,但几乎没人能够远远地甩开它。
英国与美国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,它是一个欧洲体系的福利国家,想要努力救助处于最边缘的贫困人群。艾伦瑞克发现,对美国的穷人们来说,正是房租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。当某地的土地价值增长,开发商们就会用出得起的价钱买下所有的土地和房屋,把它们变成高档公寓,穷人们就被赶到边缘地区,甚至房车公园的租金也会受住房短缺的影响而上涨。在英国,社会住房可能会把穷人限制在那些通常条件很差的贫民区,但是在所有城市的中心也仍有一些靠近工作地、可以支付得起的住房。最为重要的是,英国政府有“住房补助法案”,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私人出租房或是地方政府出租房的租金补助。保守主义者经常审视这个庞大的“住房补助法案”,但是正是这个法案,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,让英国的穷人和低收入者们避免沦为美国式的境遇凄惨的乞丐。现在,尽管那些无子的家庭还在依靠4.10英磅的最低时薪挣扎求生,只有一个挣钱者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接受“工作家庭税收津贴”。英国的国家福利制度可能并不是那么慷慨大方,但它使得这种英美不同政治文化之间的对比很微妙。
然而,芭芭拉·艾伦瑞克所报道的深层真相,不仅适用于美国,也同样适用于英国。两个国家的社会基础服务都依赖那些赚着养不活自己薪资的人。他们从事的不是一些边缘性的工作,而是一些必须要有人做的工作——在护理之家照顾老人,清洁住房和办公室,在餐厅工作,在商店服务。这些行业已经把他们的员工数删减到最低,压榨尽他们最后一点生产力。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,报酬越好,这些服务也就越少。如果最低工资被设在一个体面的标准上,挣得更多的人就不得不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进行支付。“啊”,经济学家们就会说,“那样低收入者们就会漫天要价而无人问津,只会单纯导致他们失业而已。”但是,当艾伦瑞克寻找可从事的服务性工作时,显然这些工作还是需要有人去做的。对第三世界的劳工来说,照顾老人就不是一个会消失的工作。
30年前,我曾经去过伦敦旅行,做过那些不需要任何技巧的工作,看到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浪费人们的才能,而且还是艰辛、劳累、无趣和低薪资的。我曾写过一本名为《一种工作人生》(a working life)的书,讲述了我先后一系列的工作经历,从一家位于阳光港口的肥皂厂、一家里昂蛋糕厂、一家位于伯明翰的汽车配件厂、一家医院,再到其他地方。自此以后,英国爆发了一场社会变革的大地震,见证了一个庞大的占工薪阶层总数2/3的人群上升到了白领阶层,过上了拥有自己住房的中产阶级生活,他们的子女也随之拥有了更好的教育与机会。举例来说,在1971年,7个人当中有1个人上过大学,现在是3个人当中就有1个。但是仍有30%的人被抛下了,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劳工,而且境遇比起以前还更糟。在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过程中,他们已经丢掉了传统的工会成员的身份,而这个身份在过去可以保证蓝领们拿到体面的工资。
工会成员的身份仍可以将较好与较坏的工作场所区分开来。现在只有19%的工会成员在私营部门工作(国营部门则是一个更好的雇主),而且服务业的员工们比以前更加无助。伴随着“工作家庭税收津贴”,国家开始介入到最低薪金的问题上——但是市场依据商品真实耗费而进行标价的失败,为什么要由纳税人来买单呢?
以上所有这些都是干巴巴的材料,但是芭芭拉·艾伦瑞克的书却是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读本。现在的新闻几乎不再涉及贫困的问题,而且工会也不再成为新闻题材。所有西方社会的自我形象,都被设定成有消费热点、可以向上层流动、经济持续增长和前景不断上升。在英国,平均生活标准在过去10年中上升了30%,而且可能在未来
在线试读
序 章 准备开工
这本书最初发想的地点,是在一个颇为奢华的场所。一天,《哈泼》杂志的编辑路易斯拉方(Lewis Lapham) 带我到一家法式乡村风餐厅,讨论我未来可以替他们写些什么文章。那里光一顿午餐就要价30美元,印象中我吃了鲑鱼和田园沙拉。当我们的对话转到贫穷问题上时,我对 这个比较熟悉的议题发表了一些意见,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文化有关的题材。譬如说,那些缺乏专业能力的人,到底是怎么靠微薄的薪水来生活?尤其是几近400万名的女性,她们因为福利制度修改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,又该如何靠着一小时6或7美元的薪资生存下去?接着,我就说了一句后来有很多机会感到后悔的话:“实在应该有人去做一些老式的新闻调查工作,你知道,就是自己实际到那些地方亲身体验看看。”我指的是某些比我年轻的人,某些求知若渴、有时间做这些工作的新进记者。但这时拉方脸上露出有点疯狂、要笑不笑的表情,我知道这是他下定决心时的样子。过了长长的几秒后,他吐出三个字:“你来做。”
上一次有人劝诱我舍弃正常生活去从事工时长而低薪的劳动工作,已经是70年代的事了。当时有数十名(也许数百名)60 年代的激进分子开始进入工厂,想让自己“无产阶级化”,并在过程中组织起工人阶级。但那可不是我。我同情那些父母,他们付钱让这些想成为蓝领阶级的孩子上大学,也同情这些激进分子试图加以“提升”的对象。在我自己的家庭里,低薪生活离我从来就不遥远。在许多时候,它其实让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写作生活,即便收入不高。我姐姐做过一份又一份低薪工作,包括电话公司客服人员、工厂工人和接待员。她必须一面工作,一面不断跟她所谓的“薪水奴隶的绝望感”对抗。我和已结婚 17年的先生坠入情网时,他还是一名时薪4.50美元的仓库工人。 当他最后终于逃离那里,成为卡车司机工会的组织者之一时,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。我父亲是一名铜矿工人,祖父和叔叔不是在矿场就是在联合太平洋公司工作。所以对我来说,整天坐在书桌前不只是一项特权,更是一项责任,我想替在我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发声,即便有些已不在人世。他们有许多话想说,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。
除了我自己的疑虑不安之外,有些家族成员还于事无补地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醒我,其实我可以在不影响自己研究工作的情况下进行这项计划。例如我可以改用新进人员的标准来发给自己薪水,收自己房租钱和一些生活费用如瓦斯等,然后在一个月后把这些数字加总起来就得了。若以我们镇上一般平均6至7美元时薪的薪水,租一间月租大约 400 美元的房子住,最后加总出来的薪水和支出也许可以勉强平衡。但若我们谈的是一名被摒除在福利制度外的单亲妈妈,她是否可以在失去政府协助,如食物券、医疗补助、住房和儿童照护津贴等的情况下生存,那么答案不用我出门到外头去体会就已经知道了。全美游民联盟(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)在1998年(也就是这项计划进行的那年)指出,取全美境内的平均数来计算,一个人需 要赚到8.89美元的时薪,才能租得起一间附一个卧房的公 寓。另外,公共政策前行中心(Preambl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)则估计,在符合福利政策补助资格的人之中,每97人只有 1 人能取得这种工作,赚得“让人活得下去的薪资”。 我干吗还费事去证实这些令人难过的事实呢?等到我再也无法逃避这项逐渐逼近的工作时,我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像 以前认识的一名老人,他会用计算器算好账本上的收支结果,然后再回头用笔把每一笔账目的数字算一遍,只为了确认先前的结果没错。
到头来,克服我内心犹豫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 名科学家,而事实上,我受的教育也正是如此。我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,而且并不是靠着坐在书桌前搬弄一些数字得来的。在这个领域里,你是可以天马行空地思考,但到最后,你还是必须实地下去做,投身到每天发生在自然界的混沌不明中。在自然界里,连最平凡的小地方都会冒出惊喜。也许,等我真正着手进行这项计划,就会在低薪劳工的世界里发现某些隐藏的经济原则。毕竟,如果像以华盛顿为总部的经济政策研究所(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) 在1998年所指出的一样,有30%的劳动人口都靠着8美元或更少的时薪挣扎度日,那么他们大概找到了某些我还不 晓得的秘诀,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。或许,我甚至还能像修改福利政策的那些家伙们信誓旦旦讲的一样,在自己身上发掘到所谓“走出家庭所带来的振奋心理效应”。又或者在另一方面,会有出乎意料的代价等着我去付(身体上、财务上和情感上的),推翻这一切事先的算计。无论如何,得到答案的唯一方式,就是不要怕弄脏手,走出去实际做。
秉持着科学精神,我首先决定出一些原则和参数。很显然地,第一项原则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,任何单靠我受的教育或平时工作经验就会的工作都不能选(但这么说的意思可不是征求专栏作家的广告就有一大堆)。第二项原则是,我必须在所有能做的工作中找到薪水最高的,并确实保住它。意思就是,我不能摆出马克思主义者的架势大骂雇主一番,或溜班躲在女厕所里读书。第三项原则是,我必须在安全性和隐私性尚可的前提下,尽可能找到最低等级的住宿环境。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概念有些模糊,而且后来也证明,我的标准随着时间过去也越降越低。
我努力坚持这些原则,但随着计划实际进行,我会在某些时刻稍微做调整,或甚至把它们丢在一边。例如在 1998 年春末,当我刚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的西屿(Key West)进行这项计划时,我曾跟面试者说,我能用正确的法文或德文跟欧洲客人讲“您好”,想藉此得到女接待员的工作,但这是我唯一一次泄露自己真正的教育背景。2000年初夏,在这项计划的最后一站明尼阿波利斯,我又违背另一条原则,因为我没去做当时薪水最高的那份工作。我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否有理,留待各位读者来判断。而计划进行到最后,我更是再也忍受不住怒气,放胆痛斥雇主一顿(虽然是私下地,也从来没被管理阶层听到)。
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怎么向未来的雇主推销自己,特别是该怎么解释我为何这么缺乏相关工作经验。诚实是最好的策略,讲实话但保留一些细节不谈,似乎是最容易的方式。于是我跟面试者说自己是一名离婚妇女,在当了许多年家庭主妇之后决定重回职场。这些话确实并非谎言。有时候(虽然不是每次)我会掺进一点清洁妇的工作经验。我住在西屿的时候,经常会在晚餐后帮我室友做一点清理工作,所以我就请室友帮我写介绍信,作为面试时的履历文件。此外,一般应征表格也会要求填写教育程度,在这点上,我想博士学位不会有任何加分的效果,甚至反而可能让雇主怀疑我有酗酒或更糟的问题才沦落至此。因此我把自己的教育程度定为只念了三年大学,但列出我真正读过的母校名称。结果,没人对我的背景有疑问,而在几十个雇主中,只有一个费事去确认我的介绍信。有一次,一个特别爱聊天的面试者问到我的嗜好,我回答:“写作。”而她似乎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,即便她面试我的工作就算目不识丁也能做得非常好。
- 微信号
- 网站问题、用户注册登录请联系站长,看到第一时间及时回复。
-

- 公众号
- 慧眼看每日荐书,关键字找书,新功能陆续增加中,敬请关注!
-